文心雕龍南朝梁 通事舍人 劉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 - 502間。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廿五篇,以孔子思想爲軸,經綸創作原理 ,浹洽齊梁時代及自先秦以來的文學成果,總結成一套影響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見解。
凡十卷 五十篇 總 目
|
情采第三十一 |
|||
|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 譯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 譯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 譯 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譯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譯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 譯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鎔裁第三十二 |
|||
|
情理設位,文採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熔裁,隱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斫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肬,實侈於形。一意兩齣,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 譯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 譯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核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缺,則短乏而非核;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 譯 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於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玩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衞,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聲律第三十三 |
|||
|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關鍵,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征。夫宮商響高,徵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摛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聽易爲察,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 譯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迭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迕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滋味流於下句,風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則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譯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回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譯 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不易,可謂銜靈均之餘聲,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疏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章句第三十四 |
|||
|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爲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譯 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譯 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譯 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兩體之篇,成於西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譯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 譯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於句外。尋兮字承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札句之舊體;﹁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閒,在用實切。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麗辭第三十五 |
|||
|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譯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征人資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 譯 張華詩稱:﹁游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 譯 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言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 |||
|
校對中 |
|||
|
| |||
|
|
|||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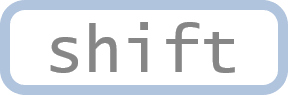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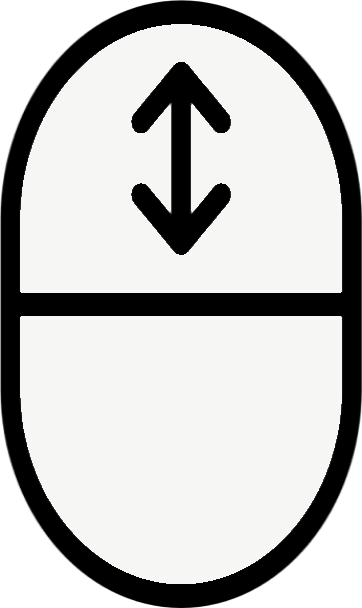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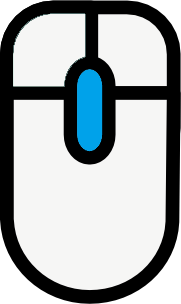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