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南朝梁 通事舍人 劉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 - 502間。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廿五篇,以孔子思想爲軸,經綸創作原理 ,浹洽齊梁時代及自先秦以來的文學成果,總結成一套影響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見解。
凡十卷 五十篇 總 目
|
神思第二十六 |
|||
|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 譯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譯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譯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①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譯 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慮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貧,辭弱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譯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譯 贊曰: 譯 評 校①有電子本作﹁沉﹂。據明弘治馮本、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作﹁思﹂。 |
|||
|
| |||
|
體性第二十七 |
|||
|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譯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譯 夫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風骨第二十八 |
|||
|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 譯 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牽課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乃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譯 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譯 若夫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晝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通變第二十九 |
|||
|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乾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譯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 譯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譯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入乎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譯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定勢第三十 |
|||
|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 譯 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譯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逾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譽兩難得而俱售也。 譯 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 譯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核,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勢有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譯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 譯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 |||
|
校對中 |
|||
|
| |||
|
|
|||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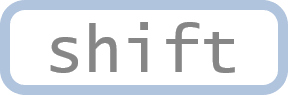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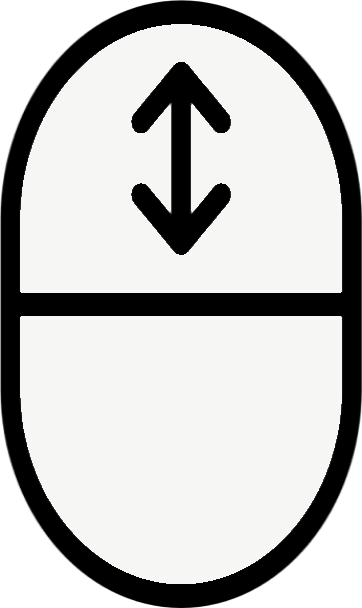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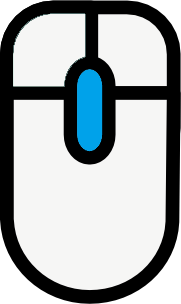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