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南朝梁 通事舍人 劉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 - 502間。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廿五篇,以孔子思想爲軸,經綸創作原理 ,浹洽齊梁時代及自先秦以來的文學成果,總結成一套影響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見解。
凡十卷 五十篇 總 目
|
銘箴第十一 |
|||
|
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鑑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於景鍾,孔悝表勤於衞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棺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誇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 譯 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閒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譯 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鑒有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勖符節,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井灶,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譯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誄碑第十二 |
|||
|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詞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其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辭,嗚呼之嘆,雖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 譯 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 譯 若夫殷臣詠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影而效者,彌取於工矣。 譯 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淒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譯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 譯 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眾碑,莫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摹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矣。 譯 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贊勛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哀弔第十三 |
|||
|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 譯 暨漢武封禪,而霍嬗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降及後漢,汝陽主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其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慮贍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 譯 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譯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併名爲弔。 譯 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反騷,故辭韻沈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譯 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末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雜文第十四 |
|||
|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辯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文。及枚乘攡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譯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間,密而兼雅;崔寔答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眾,無所取才矣。原夫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體之大要也。 譯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云所謂﹁猶騁鄭衞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譯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勖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閒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譯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諧讔第十五 |
|||
|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 譯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笑衽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 譯 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賦末。 譯 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觀夫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 |||
|
校對中 |
|||
|
| |||
|
|
|||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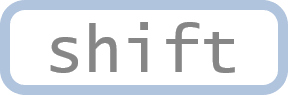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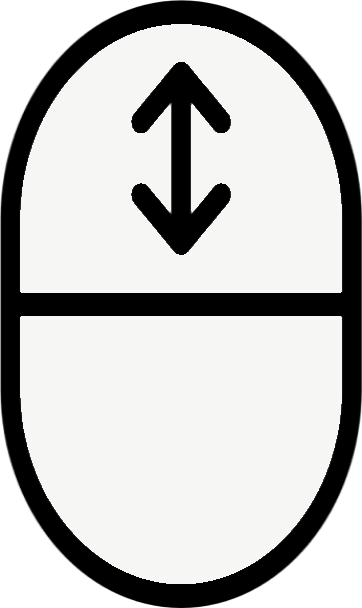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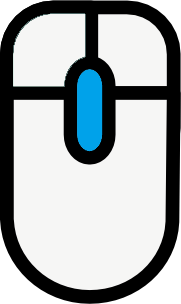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