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南朝梁 通事舍人 劉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 - 502間。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廿五篇,以孔子思想爲軸,經綸創作原理 ,浹洽齊梁時代及自先秦以來的文學成果,總結成一套影響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見解。
凡十卷 五十篇 總 目
|
指瑕第四十一 |
|||
|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 譯 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 譯 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譯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有﹁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譯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 譯 若夫註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只,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矣。 譯 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匹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養氣第四十二 |
|||
|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 譯 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技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 譯 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譯 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譯 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也,則有申寫郁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 譯 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衞氣之一方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附會第四十三 |
|||
|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採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攡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 譯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乾。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疏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 譯 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 譯 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事理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嘆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 譯 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郁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總術第四十四 |
|||
|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爲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翰曰筆,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 譯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鮮;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晰,淺者亦露;奧者復隱,詭者亦曲。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槬之中;動角揮羽,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 譯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譯 夫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時序第四十五 |
|||
|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詠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盪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 譯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譯 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宴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征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清金馬之路。子云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譯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章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皇羲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譯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於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譯 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含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譯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衝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嘆息。 譯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愈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乾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 譯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譯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 譯 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世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揚言贊時,請寄明哲!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 |||
|
校對中 |
|||
|
| |||
|
|
|||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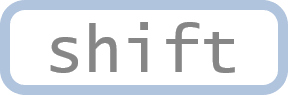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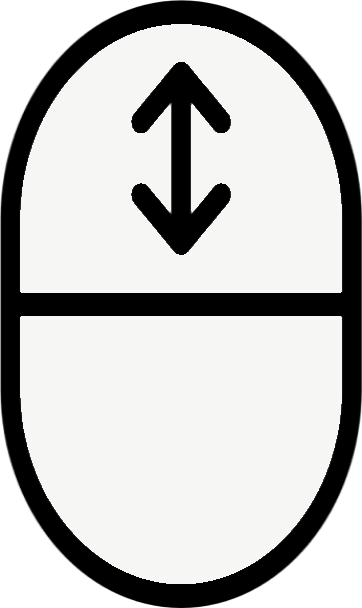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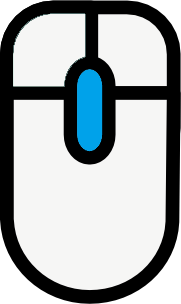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