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南朝梁 通事舍人 劉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 - 502間。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廿五篇,以孔子思想爲軸,經綸創作原理 ,浹洽齊梁時代及自先秦以來的文學成果,總結成一套影響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見解。
凡十卷 五十篇 總 目
|
明詩第六 |
|||
|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 譯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絃。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譯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譯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譯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雋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譯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樂府第七 |
|||
|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及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嘆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胥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 譯 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典,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漢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 譯 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雜盪,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之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 譯 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樂,不直聽聲而已。 譯 若夫艷歌婉孌,怨詩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左延年閒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嘆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 譯 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韋所改,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銓賦第八 |
|||
|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攡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譯 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𢭃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譯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播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 譯 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寫送文勢。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 譯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夸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篇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勛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譯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着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頌讚第九 |
|||
|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順,並謂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乃覃及細物矣。 譯 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後,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核。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雜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譯 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譯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言爲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譯 然本其爲義,事在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祝盟第十 |
|||
|
天地定位,祀遍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 譯 昔伊耆始蠟,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 譯 自春秋以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賀室,致禱於歌哭之美。蒯聵臨戰,獲祐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麗者也。漢之羣祀,肅其百禮,既總碩儒之義,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驅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譯 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唯陳思詰咎,裁以正義矣。 譯 若乃禮之祭祝,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贊言行。祭而兼贊,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視儀,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 譯 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涿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祭奠之恭哀也:舉匯而求,昭然可鑑矣。 譯 盟者,明也。騂毛旄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祝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漢晉,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 譯 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存殷鑑。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 |||
|
校對中 |
|||
|
| |||
|
|
|||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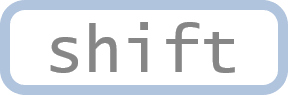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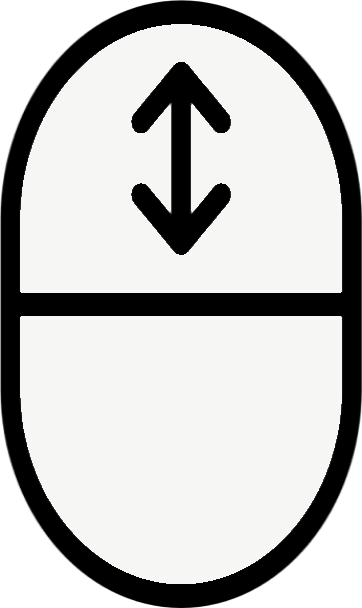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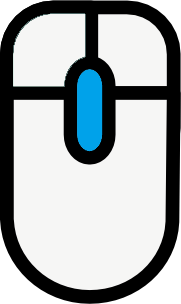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