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南朝梁 通事舍人 劉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 - 502間。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廿五篇,以孔子思想爲軸,經綸創作原理 ,浹洽齊梁時代及自先秦以來的文學成果,總結成一套影響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見解。
凡十卷 五十篇 總 目
|
封禪第二十一 |
|||
|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跡者哉?綠圖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 譯 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嶽,鑄鼎荊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諫,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勛德而已。是以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銘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 譯 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勛,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贊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讖,敘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核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 譯 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遁辭,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采,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靡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績寡,飆焰缺焉。 譯 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章表第二十二 |
|||
|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贊。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 譯 秦初定製,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職司也。 譯 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表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如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俊。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 譯 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屈,必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奏啟第二十三 |
|||
|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 譯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勛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①,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②,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勸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 譯 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譯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秦有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慾全,矢人慾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 譯 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辟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逾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御,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譯 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乾。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 譯 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矯正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言貴直也。自漢置八能,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譯 贊曰: 譯 評 校①明弘治馮本作﹁兵卒﹂,今據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作﹁兵事﹂。②有電子本作﹁辨﹂。明弘治馮本作﹁辭﹂,疑有誤,今據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作﹁暢﹂。 |
|||
|
| |||
|
議對第二十四 |
|||
|
﹁周爰咨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 譯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吾丘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之之陳於珠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譯 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采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谷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核爲美,不以環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游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 譯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者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明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 譯 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 譯 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書記第二十五 |
|||
|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 譯 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叔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云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譯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所以散鬱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譯 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爲美者也。原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譯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式;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譯 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 譯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 譯 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 譯 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 譯 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 譯 術者,路也。算曆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 譯 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登觀書雲,故曰占也。 譯 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訊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 譯 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 譯 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從也。 譯 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譯 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 譯 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 譯 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 譯 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 譯 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 譯 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 譯 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 譯 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 譯 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簽。簽者,纖密者也。 譯 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譯 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 譯 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 譯 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采以爲談,況逾於此,豈可忽哉! 譯 觀此眾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譯 贊曰: 譯 評 |
|||
|
| |||
|
| |||
|
校對中 |
|||
|
| |||
|
|
|||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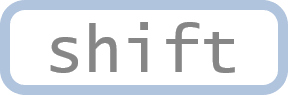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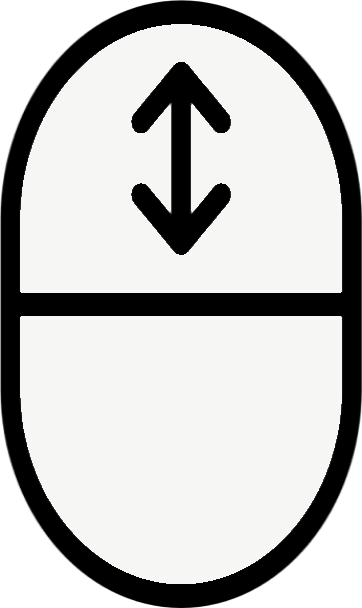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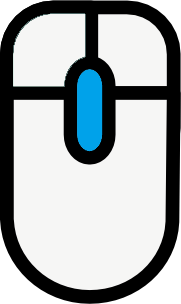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