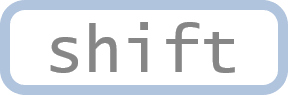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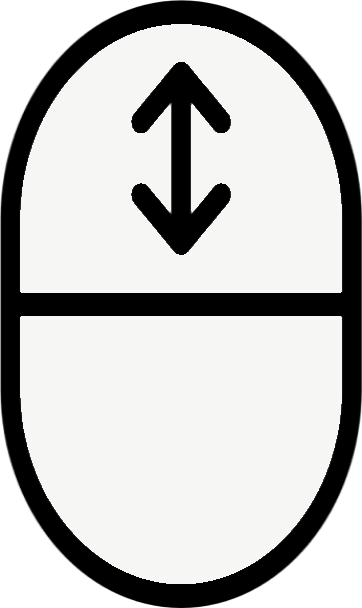 滾輪/
滾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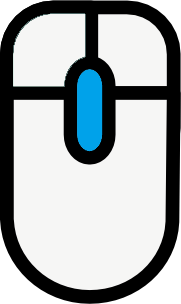 按一下
按一下
孫子十三篇整理中
春秋 齊 孫武
孫子孫子兵法春秋 齊 孫武
校勘、注釋按此顯示
注
曹操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以孫子略解(又名孫子注)傳世。後繼有(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陳皥、賈林、杜佑、(宋)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等續注。
此電子本據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整理,惟收錄曹操注。
火攻篇第十二
注 曹操曰:以火攻,當擇時日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行火必有因,曹操曰:因奸姦人也。煙火必素具。曹操曰:煙火,燒具也。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曹操曰:燥者旱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曹操曰:以兵應之也。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曹操曰: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曹操曰:數當然也。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曹操曰:取勝明也。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曹操曰:水但能絕敵糧道、分敵軍,不可奪敵蓄積。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賞善不逾日也。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曹操曰:不以己之喜怒用兵也。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篇第十三
注 曹操曰: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注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不可象於事,曹操曰: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於度,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必取於人,曹操曰:因間人也。知敵之情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生間者,反報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曹操曰:舍,居止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曹操曰:伊尹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曹操曰:呂望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孫子序 魏武帝曹操 策
注
選自曹操集。三國時期魏國政治領袖、軍事家曹操,整理孫子十三篇。據唐代杜牧考據,古籍之中傳頌的孫子兵法原有數十萬言,疑是參合了各家兵法論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共輯十三篇,並為之註釋,編成孫子略解世稱孫子注,今存。兩卷,成為流傳下來的據本,亦屬最早的註釋本,世稱曹注本。近世自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翻譯出的古本孫子十三篇,字句與曹注本大同小異,可是排序不順,行文不暢,不及今本結構清晰,條理分明。古本孫子的整理,是否全為曹操一人之功,至今尚未能定奪,然而漢簡古本之發現,推翻了小說三國演義第六十回指曹丞相剽竊孫子,改成自己的孟德新書。曹丞相當年不僅未有剽竊,既博覽兵書,在整理過程中,將孫子與其佚篇或偽篇區分開來,排整疏理,更創先河評注孫子,唐宋大家紛紛補筆,為後世兵法研究貢獻豐碩。
﹁曹公五書﹂之首孫子略解,曹操為之序,原文如下。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恕,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
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有孫臏,是武之後也。
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校
此篇名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自﹁孫子者……補文﹂五十字,據太平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即謂此文。
上述校案語兩則,詳見清 光緒三年 平津館本 重校刻二十二子。
按
二十世紀末,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子兵法,比曹操輯注所據本理應更早,其中十三篇之外,尚有佚文,未知為何曹操未有輯錄。學者經過多年考究,一說是古本孫子兵法到了曹操手上,餘下佚文已散失;二說是曹操曾經審閱過文句而決定削減,據傳他結集這些剩餘的兵法論集又輯成了續孫子兵法,可惜此書早已失傳。三說該竹簡文本有部分屬於偽作,又或與齊孫子,即孫臏所作兵書混淆了,遂由曹操整理出來。眾說紛紜,至今學者對銀雀山漢簡文本真偽的推論仍有分歧。
無論如何,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子兵法篇名仍存,待考如下:
︻吳問︼
︻四變︼原無篇名,由竹簡整理者據文義補擬。
︻黃帝伐赤帝︼
︻地形二︼殘缺過甚。原篇名作﹁ 刑二﹂,竹簡整理者認為缺字為﹁地﹂。
︻見吳王︼部分文字無法排比接續。原無篇名,由竹簡整理者據文義補擬。
︻程兵︼僅存五字。
另外清代學者畢以珣孫子敘錄和王仁俊孫子佚文也收錄了傳世文獻中留存的孫子佚文。
清人畢以珣孫子敘錄和王仁俊孫子佚文曾廣為搜輯。現今出土漢簡佚文研究,見如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張妍、蔣魯敬、劉玉玲、楊安、張海波之論文及衛松濤、楊青之期刊投稿等多種著作。
孫子本傳
載於宋本 十一家注孫子
注
出土漢墓簡本並無孫子之傳,此傳錄自十一家注孫子,校勘所見與今本史記互有不同。例如魏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或十三年之句仍須考查。
詳見:
史記卷六十五、列傳第五 孫子吳起列傳清 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孫子平津館本 重校刻 清 光緒三年 浙江書局 1877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藏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
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
對曰:﹁可。﹂
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
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
婦人曰:﹁知之。﹂
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
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鯨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
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
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
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孫子注作鬬,見李零古本研究考。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田忌從之,魏果去那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
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竪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并序
載於 鄭樵 通志 藝文略 孫子遺說一卷
滎陽 鄭友賢 撰
序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 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 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 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深。 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 頃因餘暇,摭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
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擊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眾,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為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多、少、無之義?
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為多,得一二者為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為多,得二三者為少。五七俱得者為全勝,不得者為無筭。所謂冥冥而次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
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困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
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為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為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
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奉,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㓂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
曰:餘法概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誡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為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
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隨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鬥孫子注作鬬,見李零古本研究考。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概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為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為覆軍。﹂惟公得武法之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為歟?
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 不能彊使為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為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肄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疏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 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
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彊弱為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實彊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妙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彊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 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
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為受敵,以勝為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
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
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為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
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為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為虛,變虛而為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 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鬥孫子注作鬬,見李零古本研究考。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眾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敗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 動也、 生也、 有餘也者, 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 內以虛實之法愚士眾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 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 皆虛實之類, 不可拘也。 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 皆倣於此, 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軍之與眾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
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為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眾爭為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眾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眾爭者,舉軍而趨也。為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為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
曰:兵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為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為變。蓋本仁者治必為義,立詐者動必為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眾皆法也,獨稱此用眾之法者,何也?
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眾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眾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 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
曰:三軍主于鬥孫子注作鬬,見李零古本研究考。下同。,將軍主于謀。鬥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鬥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鬥,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鬥, 上者不能謀, 敵人上下怯亂, 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鬥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 奪謀心也。 三軍、 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 何也?
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為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為智。用兵之法,出於眾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眾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復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 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
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氾、 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眾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為篇異也。李筌以﹁途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為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為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
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蒭牧樵採之利;四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興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 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
曰:恐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 曰走、 曰弛、曰崩、曰陷、 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 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眾如群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 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為二句者何?
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 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為縛,或謂縛馬為方陳陣者,何也?
曰:解方為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彊為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為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為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
曰:不可探測而蘊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誡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誡備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為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陣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
曰:興師動眾,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壃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為越人之國, 如秦越晉伐鄭者, 鑿也。
或曰:不知諸侯之謀, 不能預交;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 不能行軍;不用鄉導, 不能得地利。 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 何也?
曰:此三法者, 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為直,後發先至之為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為客深入利害之為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塗,若非和鄰國之援,為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為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 不其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
曰:治軍御眾,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眾,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 噫! 常法之賞,不足以愚眾;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 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驅群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眾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
曰:用間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使間者,使人為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為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
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為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為間于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于篇之末?
曰:用兵之法,惟間為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于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 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 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為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為深,而以計為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說篇終
附︻答話︼并序輯各散佚文獻
注 孫子佚文是指傳本十三篇之外見於其它文獻,並冠以孫子之名的文字材料。孫武追隨吳王為將之後,與吳王就兵法問對,共十四篇。這類語錄原撰者雖然不詳,然而其中唐人杜佑通典收錄較多,論及各種軍情地勢,共十一篇。同時,孫子何注、張注及文選注等亦有零星徵引。︻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三篇,錄自銀雀山出土漢代竹簡孫子兵法殘文,續見︻地形二︼、︻程兵︼、︻見吳王︼等篇,由於文字殘甚,無法說明全文大意。至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子集成等書,存錄占卜吉凶的內容,疑為後人偽托,故未有收錄。清人畢以珣孫子敘錄和王仁俊孫子佚文曾廣為搜輯。今參照各文獻,僅供研究參考。
論散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
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擊懈怠,可以有功。﹂
論輕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
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徉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
又據何氏注引補
武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論爭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
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慾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論交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絶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絶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為寡又均,則如之何?﹂
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論衢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
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為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膽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論重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
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輪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實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論圮氾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氾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
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裏,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論圍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絶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
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並炊數日,無見火煙,故?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陣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鬥後拓,左右犄角。﹂
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
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論反圍攻與圍攻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勵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
武曰:﹁深溝高壘,示衆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實,割發捐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並氣一力,或攻兩勞,震鼓疾噪,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
武曰:﹁山峻谷險,難以逾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絶其糧道,恐有奇隱而不睹,使吾弓弩俱守其所。﹂張預按︰何氏引此文,亦云﹁兵法曰﹂,則知問答之詞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論死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虞,兵眾而強,圖之奈何?﹂
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令無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論山地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
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採太平御覽作禁其牧采,依通典。。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論將 見 通典 卷一五九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又據 左傳 孔疏哀西元年
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灶未炊,將不言飢。﹂
論兵陣 見 文選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李善注
孫子兵法:﹁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遊暇譽豫,令猶行也。﹂
孫子又曰:﹁長陣為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第四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
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
吳王曰:﹁何謂也?﹂
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
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
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補 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心,猶璧玉之不可污也。﹂太平御覽以為出於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為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為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畧焉︰上畧伐智,中畧伐義,下畧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即名為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吳問︼銀雀山漢墓殘簡 154-161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
孫子曰:﹁笵、中行是氏先亡。﹂
﹁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
﹁孰為之次?﹂﹁韓、巍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吳王曰:﹁其說可得聞乎?﹂
孫子曰:﹁可。笵、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為𡟰畹,以百六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田陝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為𡟰畹,以百八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田陝,置士多;……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笵、中行是氏次。韓、巍魏制田,以百步為𡟰畹,以二百步為畛,而伍稅之。其□田陝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智是氏次。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為𡟰畹,以二百册步為畛,公无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僉臣收,以禦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
吳王曰:﹁善。王者之道,□□厚愛其民者也。﹂ 二百八十四
︻四變︼銀雀山漢墓殘簡 2685 162-171
□□□□□徐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令有所不行。
.徐途之所不由者,曰:淺入則前事不信伸,深入則後利不椄接。動則不利,立則囚。如此者,弗由也。
.軍之所不𣪠擊者,曰:兩軍交和而舍,計吾力足以破其軍,獾其將。遠計之,有奇埶勢巧權於它,而軍……□將。如此者,軍唯雖可𣪠擊,弗𣪠擊也。
.城之所不攻者,曰:計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於前,得之而後弗能守。若力不足,城必不取。及於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為害於後。若此者,城唯雖可攻,弗攻也。
.地之所不爭者,曰:山谷水澤旡能生者,□□□而□□……虛。如此者,弗爭也。
.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變者,則弗行也。……行也。事……此四變者,則智知用兵矣。
︻黃帝伐赤帝︼銀雀山漢墓殘簡 172-177
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右陰,順術,倍背衝,大烕滅有之。□年休民,孰熟榖,赦罪。東伐蒼帝,至於襄平,戰于平□,右陰,順術,倍背衝,大烕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戰於□□,右陰,順術,倍衝,大烕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剛,戰於□□,右陰,順術,倍衝,大烕滅有之。已勝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歸之。湯之伐桀也,至於□□,戰于薄田,右陰,順術,倍背衝,大烕滅有之。武王之伐紂,至于■遂,战牧之野,右陰,順術,倍背衝,大烕滅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地之理、民之請情,故……
按
︻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三篇,錄自銀雀山出土漢代竹簡孫子兵法殘文,世稱簡本。不過有學者曾考查︻吳問︼篇與先秦史實及田制有不符合之處,疑是偽托之作。還有其它逸文,如銀雀山出土的︻地形二︼、︻程兵︼、︻見吳王︼等篇,由於文字殘甚,無法說明全文大意,此電子本暫不收錄。期待研究成果不斷,文史學者繼往開來。
校對凡例:
一、參考資料為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 1985、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文物出版社 2010、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 1985、銀雀山漢簡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文物出版社 1989,整理電子本。據張海波銀雀山漢墓簡牘集成︻貳︼、︻叄︼文物出版社 2021及其論文及衛松濤之期刊投稿等修訂釋文及標點。
二、殘缺內容難以判斷者,以□表示猜想文字,以■表示實有字而無法隸定;可隸定卻無法輸入,亦以■表示。
三、擬補之殘文加灰框標示,擬補之缺文加紅框標示。殘缺內容字數難以估計者,以……作標示。
四、異體字下以小字標示正體字。
孫子孫子兵法春秋 齊 孫武
校勘、注釋按此顯示
參考版本
原本: 十家孫子會注 宋史 藝文志 南宋 吉天保 輯 1131-1161
底本:宋本 十一家注孫子 南宋 吉天保 中華書局影印本 1961
據本: 孫子 平津館本 重校刻 清 光緒三年 浙江書局 1877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藏
竹簡本: 銀雀山漢墓竹簡抄本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 1976
載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文物出版社 1985
載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文物出版社 2010
銀雀山漢簡釋文吳九龍 文物出版社 1985
殘簡: 大通上孫家寨漢簡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 漢簡殘片 載自文物 1981
晉殘本: 六朝鈔本舊注孫子 新彊吐峪溝 斷片 載自孫子集成 齊魯書社 1993
治要本: 魏武帝註孫子 載自唐 群書治要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本 1967
曹註本: 宋本 魏武帝註孫子 清 平津館刊 顧千里摹本 載自孫子集成 齊魯書社 1993
武經本: 宋本 武經七書 北宋 元豐年間 朱服 輯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學藝社借照 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 載自孫子集成 齊魯書社 1993
四庫本: 孫子兵法 載自文淵閣四庫全書 兵部類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1983
孫校本: 孫子十家註 孫星衍校本 清 嘉慶二年 兗州觀察署刊本 1797
櫻田本: 古文孫子 日 櫻田迪 家藏抄本 服部千春孫子兵法新校 1997 附
書目
校注
魏武帝注孫子 又稱孫子略解、孫子注 曹操 注 清平津館刊 顧千里摹本
武經七書 北宋 元豐年間 朱服 輯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學藝社借照 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
十家孫子會注 宋史 藝文志 南宋 吉天保 輯
宋本 十一家注孫子 中華書局影印本 1961
孫子參同 明 李贄 評注 閔于忱 輯
孫子古本研究 李零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評釋
孫子章句訓義 錢基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吳孫子發微 李零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孫子兵法譯注 按孫子譯注補入曹操注 郭化若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工具書
孫子集成 按謝祥皓 劉申寧 輯 濟南齊魯書社 1993
孫子兵學大典 按邱復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編者案:因電子檔每頁字碼過大,於不同裝置上或有缺漏、跳段、格式錯置等技術問題。
如見狀,煩請轉告開發人員,將盡力解決,以備妥善,方便後學。